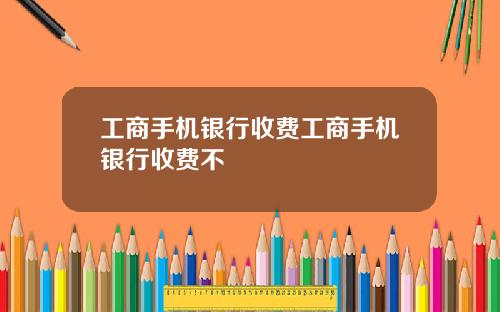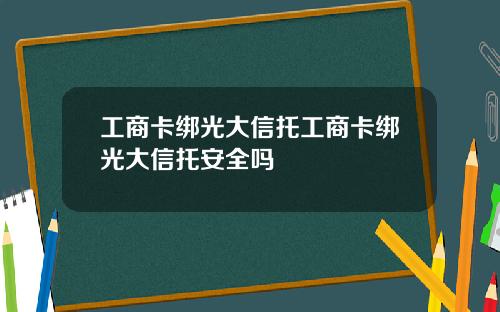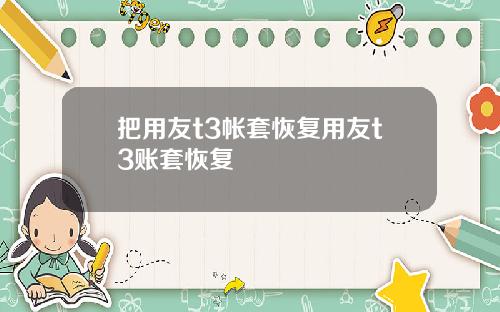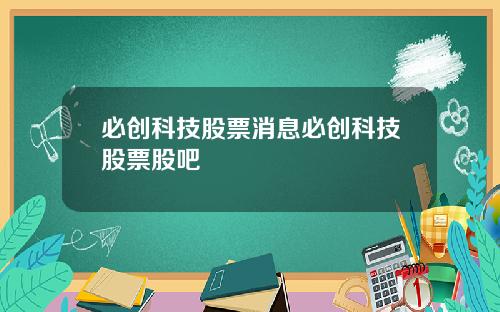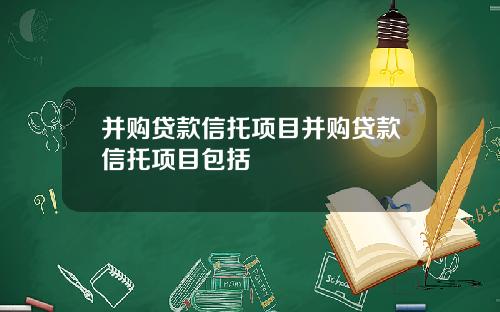铝合金门窗花格图片大全
文章目录:
1、剪窗花过年 春联门神福字窗花和吊钱过年之前必备2、幕府路金达花园 镂空花格吊顶3、江苏85后博士花5万,改造自家宅基地:整个家都不一样了
剪窗花过年 春联门神福字窗花和吊钱过年之前必备
过春节,一般年前最忙。到大年初一,人们就可以尽享清福,阖家欢乐了。年前,男主人、女主人都要外出忙着采购年货,一些妇女和孩子留在家里,洒扫庭除之后,围坐在炕头和桌前,开始剪窗花了。
这样的风俗,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剪出的窗花贴到窗上,和大门两旁贴的春联、大门中央贴的门神、屋子墙上贴的福字,和房檐门楣上挂的吊钱,一定都要在大年三十之前完成,才算是过年的样子。清末竹枝词里说:“扫室糊棚旧换新,家家户户贴宜春。”其中的“贴”字说的就是准备过年这样必需的程式。
另一面,和过年的时候家里人不许动刀剪的民俗有关(还有不许扫地倒脏土等,都是防止不吉利的说法)。清时诗人查慎行有诗:“巧裁幡胜试新罗,画彩描金作闹蛾。从此刀剪闲一月,闺中针线岁前多。”这里说的巧裁新罗,画彩描金,就包含有剪窗花,从此刀剪闲一月,后来改成到正月十五;再后来到破五;现在,已经彻底没有这个风俗了。
春联、门神、福字、窗花和吊钱,这五项过年之前之必备,我称之为过年五件套。和后来结婚时候一度流行的手表、自行车和大衣柜这三件套的说法相类似。只是,结婚三件套,早已被时代的发展所淘汰,而过年这五件套,几百年过去了,至今依然风俗变化不大,除了吊钱如今在北京见到的少了,其余四种,仍然在过年前看许多人家在忙乎张罗。因为这是过年必备的庆祝仪式的硬件标准。可见,民俗的力量,在潜移默化中,代代传承。
到正月十五灯节之前,再加上各家大门前挂上一盏红灯笼,就是过年必备的六件套。这六件套,全部都是红颜色,过年前后这一段时间里,全国各地,无论乡间,还是城市,到处是这样一片中国红,那才叫过年,是过年的色彩。如果说过年到处是这样红彤彤一片的海洋翻滚,那么,窗花是其中夺目的浪花簇拥。
过去的岁月里,年前要准备的这五件套,除了门神尉迟恭秦叔宝的形象复杂,要到外面买那种木刻现成的之外,其余四件,普通百姓人家,都是要自己动手做的。这和年三十晚上的那顿饺子必须得全家动手包一样,参与在过年的程式之中,才像是过年的样子。普通人家剪窗花,是和贴春联、挂吊钱,包括做门神、写福字一样,都只用普通的大红纸。各家都须到纸店里买大红纸。大红纸畅销得很。
那时候,家附近有两家老字号的纸店,一家是南纸店,叫公兴号,在大栅栏东口路南;一家是京纸店,叫敬庄号,在兴隆街,我们大院后身。家里人一般都将这项任务交给我们小孩子,我们都愿意舍近求远去公兴号,一是那里店大,纸的品种多;二来路过前门大街,到处是卖各种小吃的店铺和摊子,我们可以将买纸剩下的钱买点儿吃的解馋。家里人都嘱咐我们买那种便宜的大红纸。其实,不用嘱咐,我们都会买最便宜的,这样剩下的钱会多点儿,买的吃食也会多点儿呢。
有一阵子,公兴号流行卖一种电光纸,我们又叫它玻璃纸,因为它像玻璃一样反光,一闪一闪。我们都喜欢,便买回家。家里大人不乐意,看着就撇嘴,让我们立马儿拿回去换纸,一准觉得还是传统的那种大红纸好。
过去年月里普通人家房子的纸窗,贴的都是高粱纸,很薄,透光性好。传统的大红纸也很薄,做成窗花,贴在这样的花格纸窗上,很是四衬适合。清末《燕都杂咏》有一首说:“油花窗纸换,扫舍又新年。户写宜春字,囊分压岁钱。”诗后有注:“纸绘人物,油之,剪贴窗上,名‘窗花’。”诗中所说的油花窗纸,指的应该就是这种高粱纸,红红的窗花贴在上面,红白相映,屋里屋外,看着都透亮,红艳艳的,显得很喜兴。电光纸厚,贴在这样的花格纸窗上,不仅不透亮,还反光,没有那种里外通透的感觉。确实是什么衣配什么人,什么鞍配什么马,传统的窗花用纸,和老式的纸窗两两相宜。老祖宗传下来的玩意儿,有它的道理。
后来,经济条件好些了,各家的窗子换成玻璃的,还是觉得贴这种传统大红纸剪成的窗花好看。那种电光纸,到底没能剪成窗花,亮相在我们的窗户上。
窗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既是手艺,也是民俗;既可以是结婚时的装点,更形成了过年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窗花的历史悠久,有人说自汉代发明了纸张之后就有了窗花,这我不大相信,纸张刚刚出现的时候,应该很贵,不可能普遍用于窗花。有人说南北朝时对马团花和对猴团花中就有了锯齿法和月牙法等古老的剪纸法;有人说唐朝就有,有李商隐的诗为证:“镂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也有人说窗花流行于宋元之后……总之,窗花的历史悠久。
我私下猜想,窗花最初是用刀刻,然后转化为剪裁。刀刻出的图案,应该受到过更早时的石刻或青铜器的雕刻影响,艺术总是相通的,相互影响和借鉴是存在的。从石刻到剪纸,从刀到剪,只是工具和材料的变化而已。剪和刻的区别,还在于剪是要把纸先折成几叠,是在石头上无法做到的。别看只是这样看似简单的几叠,却像变魔术一样,让剪纸变成了独特的艺术。
窗花,应该是剪纸的前身。窗花也好,剪纸也好,不像石刻或青铜器雕刻,多在王公贵族那边,而是更多在民间,其民间的元素更多更浓。窗花,又是农耕时代的产物,所以,它的内容更多的是花草鱼虫、飞禽走兽、农事稼穑、民间传说、神话人物,以至后来还有八仙过海、五福捧寿等很多戏剧内容,可以说是花样繁多,应有尽有。只有正月十五灯节时的彩灯上描绘的内容,可以和窗花有一拼。灯上的图案,在窗花上大多可以一一找到对应,只不过,在窗花上删繁就简,都变成大红纸一色的红。这便是窗花独到之处,一色的红,配窗子一色的白,如果过年期间赶上一场大雪,红白对比得格外强烈,就更漂亮了。
民间藏龙卧虎,窗花有简有繁。有的很丰富,我从来没有见过。前面所引的《燕都杂咏》诗后还有一注,说有这样的窗花,是“或以阳起石揭薄片,绘花为之”。这种类似拓印式的窗花,我没见过。《帝京风物略》中说:“门窗贴红纸葫芦,曰收瘟鬼。”这风俗和年三十之夜踩松柏枝谓之驱鬼的意思是一样的。大年三十的夜晚,踩松柏枝,我没有踩过,那时我们院子里有人买来秫秸秆,让我们小孩子踩,意思是一样的。但是,这种贴红纸葫芦的窗花,我也没见过。《燕京杂记》中说:“剪纸不断,供于祖前,谓之‘阡张’。”过年期间,如此夸张的剪纸,是窗花的变异,我更是没见过。
小时候,我看邻家的小姐姐或阿姨剪窗花,顺便要几朵,拿回家贴在窗上。我有了儿子之后,孩子小时候磨我教他剪窗花,我不会,便把他推给我母亲,告诉他:奶奶会,你找奶奶去!其实,奶奶只剪过鞋样子,哪里会剪窗花?但被孩子磨得没法子了,只好从针线笸箩里拿出剪子,把大红纸一折好几叠,便开始随便乱剪一通。谁想到,儿子把红纸抖搂开一看,尽管不知道剪的是什么图案,但那样像抽象派的图案,还挺新鲜,挺好看呢!这样剪窗花,一点儿都不难嘛,儿子抄起剪刀,也开始学奶奶的样子,剪出一床窗花来。我家那年春节的窗户上,贴的全是奶奶和她的小孙子剪的窗花。
流年似水,一晃又到春节。儿子的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十岁了。他们跟爸爸新学会了剪纸,年前剪了一堆的窗花,比他们的爸爸当年剪得有章法多了。虽然人在国外,但两人准备春节前送给每个同学一个窗花,让他们那些外国同学也知道中国人过年贴的窗花是什么样子。视频通话的时候,我让他们两人先别忙着把窗花送同学,一人选出自己最得意的一个窗花,先送给我。今年贴在我家的窗上,他们和他们的窗花,陪我们老两口一起过年。(肖复兴)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幕府路金达花园 镂空花格吊顶
先来做个预告,今天的目的地是幕府路金达花园,话说木工刚刚结束~看看过道吊顶里面做个镂空花格效果还挺不错的。等我拍完分享照片和视频吧! 最近南京一直处于闷热闷热的状态,这一下雨一定又是半个月停不下来,马上就要到梅雨季节了~袜子内裤表示很忧伤
江苏85后博士花5万,改造自家宅基地:整个家都不一样了
85后建筑师陆少波,
是一位从江苏常熟农村走出来的建筑博士。
2019年,他回乡改造老家的自宅,
为父母打造一栋养老房。
▲
摄影:肖潇
他以18㎡的灶间为核心,
撬动整个271㎡的宅院生活。
?成本不到5万块,?材料多为废弃旧砖,
?改造多是“微小的动作”,?房子向后退一步,
?让位于陪伴三代人的榆树、桂花树、水井、洗衣台……
?如今,父母更频繁地使用灶台做饭,
甚至捡起祭祀灶神的习俗。
在大规模的农村建设浪潮中,
这栋宅子气质异常朴素、内敛,
却显得高级、更富人情味,有淡淡的诗意与美。
陆少波说:
“这个农宅改造只是微不足道的一抹痕迹,
但我期待以此面向喧闹嘈杂的当下现实。”
?自述:陆少波
?编辑:陈 沁
近些年,我在上海、杭州、常熟三地来回跑,如今却更频繁回老家生活和工作。
“灶间之家”位于江苏常熟东部的一个小村庄,沿着村落边的道路可往南经由太仓、昆山直抵上海,离上海、杭州等地的交通,都在1-2小时内。村落本身是常熟水乡的一部分,周边有农田环绕,又紧邻工业园区。从景观上说,也是现代化城市环境的一部分。
▲
?灶间和院子原貌
▲
?灶间和院子改造后对比(摄影:肖潇)
这栋农宅,最早是爷爷奶奶在上世纪80年代盖的一层木结构小房子。1994年,我父母翻新了原来木结构的房子,重建了一栋两层的砖混住宅。所以,这座老宅有我爷爷奶奶,我父母和我三代人的共同记忆。?
我从小就对院子的两棵大树、水井印象深刻,父母也喜欢在夏天用灶台烧了玉米、绿豆汤在巷子边吃边休息。秋天的时候,院子的桂花树开花特别香,桂花树是小时候家人从边上农田移栽进来的,榆树则是爷爷种的。而我自在外求学、工作之后,就很少回来。
▲
在灶间做常熟特色蒸菜
▲
?一家人相聚的时光
?几年前,父母退休了,灶间早已废弃,屋顶也有漏水的问题,他们一直希望可以把灶间重新翻新一下。我自己对民居的研究非常感兴趣,也希望做一些跟传统乡村民居相关的设计。
我最早在中国美术学院学建筑设计,后来在同济大学和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念硕士期间,就想以家乡为题做一个相关的设计,在上海交通大学念博士时,也在继续江南水乡和上海城市研究,但是怎样改造承载了乡村日常生活的灶间,一直犹豫没法确定满意的思路。
▲
颜文樑的画作《厨房》
▲
陆少波改造后的灶间内部
?2019年,我去苏州沧浪亭参观时,偶然见到中国早期现代画家颜文樑的画作《厨房》:光线透过花格窗进入灶间,小孩在消磨着时光,各种日常的物件并置层叠,互相之间没有等级。忽然触动良多,改造的思绪才渐渐梳理出来。?
▲
井院新增的绿色水磨石水池和钢木亭子(摄影:肖潇)
整个改造的造价实际上是比较低的,材料的话不到1万块,人工费大概是3万多。红砖基本都是回收利用的,来自被拆除的农田棚子。只是增加了钢木混合的亭子和绿色水磨石的水池,跟边上的绿树形成一种颜色的呼应。
不少建造都是自己和家人亲力亲为,比如雨棚配筋、清洗旧砖。改造的施工大概就花了三四个月时间,在2019年10月份,完成了整个改造施工工作,一直住到现在。
▲
从灶间移步树院
一家人在榆树下吃蒸菜“东乡一品锅”
?常熟地区的灶间具备祭祀灶神的功能,也是吃饭的地方,家人的聊天闲谈也大多发生在这里,我童年时期关于家庭的大部分记忆都和灶间相关。?
整个改造的理念,是希望以非常微小的动作,譬如改造一个灶台,一个水井,甚至一扇小窗,一个树池,最终形成一个真正跟家的生活关联的整体。
▲
灶间联动着树院、巷院、屋院、树院
▲
灶台边储藏间的屋顶去除后,形成内院一景(摄影:肖潇)
?格局上,把灶台边上储藏间的小屋顶去除,变成了一个小内院。父母对于减少了储藏间屋顶的改造方式,觉得很不理解。农村拆迁本身就是按面积来算的,减少面积,就是减少了潜在的拆迁费用。
但去除部分屋顶的轻巧动作,让附属小屋的灶间,由原来的尽端空间变成为整个院子的中心,对整个院子的气质带来很大的改变。
▲
?灶间之家改造草图
?原来的巷道变成了一个巷院,原有的大院子划分为树院和井院,这样一来,四个小院子串联在一起,围绕着18m2的灶间。
▲
?原灶间入口改为窗,从灶间望出去可看到巷院(摄影:肖潇)
▲
灶台墙上的牡丹墨画(摄影:肖潇)
▲
松木上的疙瘩瘢痕与榫卯细节
?灶台墙上的墨画,是请当地的老师傅来画的,比如说寓意吉祥的牡丹、八仙过海。
在门窗的改动上,主要把原来灶间的入口改为窗,入口更换到新增的小院,拉长流线。木料是很便宜的松木,结合榫卯的制作方法,用清漆保留木纹的肌理,表面不平整的疙瘩,也蕴含一种很朴素的美。
▲
?陆少波的姑父在炸爆鱼
?紧邻灶台的窗户,变成了大面积的玻璃,做饭的时候,能够直接感受到院中的榆树、桂花树,还能看到天空云彩的变化。
巷院原来是一个小巷道,如今变成一个休息空间。夏天的时候,穿堂风吹过,也不需要开空调,就可以在树荫下面乘凉。还做了一个小凹龛来放东西,小朋友也爱在这儿玩耍嬉戏。
▲
?门洞落水细节与建造过程(上图摄影:肖潇)
在主屋与附属屋之间的巷弄末端,我还增加一个砖砌门洞,在空间上微弱划分了巷道和主院,也可以兼作主屋边门的雨棚和屋顶落水的排水口。雨特别大的时候,就像溪水一样汇入到整个院子的出水口。?
在主院内,既存的水井上加建了一个钢木混合结构的亭子。镂空的空间可以用来放竹竿,家人洗衣服、晒被子都比较方便。?
▲
树院里的榆树和桂花树
?树院的两棵树,榆树已有40来年历史,桂花树也有20多年。附近的鸟经常光临这两棵树,甚至有鸟在树上筑巢。
我自己经常待在灶间边上的书房,工作的时候听着鸟鸣声,看着树影斑驳,非常惬意,和城市里疲于奔命的生活状态非常不一样。
▲
?陆少波和父母在采摘春季的葱与草头(金菜花)
?原来父母上班很忙碌,长三角地区的农村生活其实是很嘈杂的,改造的灶间和院子,对生活有一种宽容感,父母的生活更多发生在其中了。
比如原来父母主要的活动区域是屋内,或者新式厨房和餐厅,如今更多回到了灶间。常熟一带特有的蒸菜也最适合在灶台的锅上蒸,父母还重新捡起来祭灶神的习俗。他们也更频繁地使用水井,花了更多的时间去打理院子和植物,还不自觉地想把之前的荒地重新种上菜。
▲
?书房可望见树影婆娑
▲
陆少波的儿子在水池玩耍
?小朋友很喜欢在灶间的窗台上面玩过家家的游戏,或者用手摇式的水泵压水玩。他们会想象井院中的木亭子像床一样,可以躺在上面乘凉。院子所激发的小孩子的想象,也让我挺意外的。
我也有计划在未来把工作室放在老家,一方面现有的交通、网络,能够让自己实现居家办公,另一方面,也希望过一种和自然乡村更亲近的生活。
▲
?灶间之家外景
?现在流行的乡村改造,或者耗费大量的钱财,最常见的就是豪华的西式别墅,比如在外立面用特别昂贵的材料,更多是一种身份的体现。又或者希望实现一种“符号化”的乡愁,所谓怀古,热衷于使用传统的材料,实际上它又变成了一种对象化的审美。
我理解的农村生活,它不只是视觉上的田园风光,本质上更是一种非常朴素的农业劳动。大家对于农村的想象,比如现在这个季节,热衷去农村观看油菜花田。或许只有作为游客时,我们才会欣赏油菜花的美。
但是,对农民来讲,油菜花田并不是一种视觉的存在,而是从油菜播种到油菜花开,再到结菜籽,最后榨菜油的过程,这种过程性的劳作,是跟日常的生活密切相关的。
灶间之家整个改造过程,多是就地取材,废料重新利用,或者是很便宜的新材料,我想打造的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没有压迫感的空间。
无论是传统的青砖瓦和大小木料,还是作为现代工业产品的水磨石、胶合木、钢板材料,只有被组织成和生活行为相关的物件时,家的日常意义才会显现。?
▲
陆少波和儿子在树院种辣椒
在我决定告诉家人改造设想前的初秋某日,父亲用手机发来一段院中榆树的视频,纷繁的枝叶在微风吹拂下沙沙作响,同时父亲留言“亭亭如盖也”。
我不知为何父亲会想起明代文人归有光在《项脊轩志》中记录旧屋老树的名句。但古人关于家的记忆的一个名句,也勾起我对这个房子的很多记忆。
归有光在文中的回忆是绵密深情的,一座陋室记录着数代人的生活痕迹。借由这一名句,不同时空下的情感记忆奇妙地交汇在一起,我越来越频繁地愿意回到故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