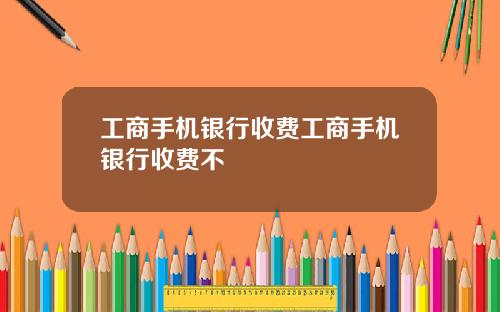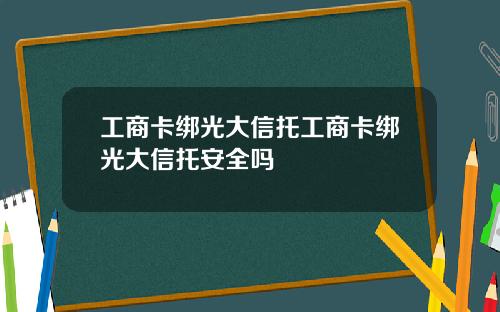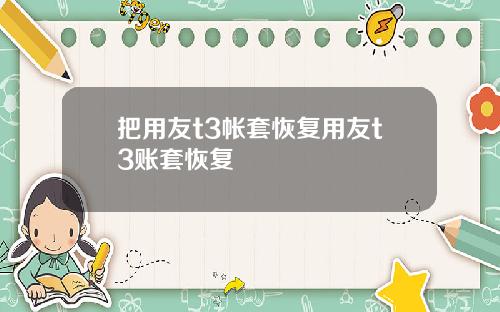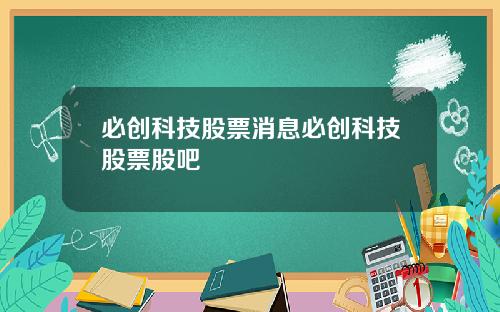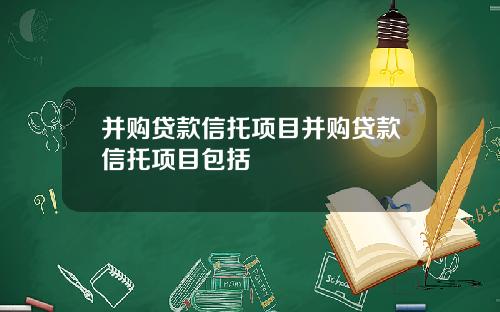钟祥铝板厂
文章目录:
1、决战决胜谱新篇·文化扶贫在行动 钟祥:楚韵今风莫愁村 文旅融合新典范2、雕刻时光(大地风华·走进古村落)3、悲情“水都”丹江口:贫困县居民一生都在搬迁
决战决胜谱新篇·文化扶贫在行动 钟祥:楚韵今风莫愁村 文旅融合新典范
文化扶贫看湖北【决战决胜谱新篇·文化扶贫在行动 钟祥:楚韵今风莫愁村 文旅融合新典范】“青砖黛瓦,门窗雕花,石路蜿蜒,置身其中,仿佛能触摸历史的记忆。篝火晚会、民间杂耍、非遗技艺、传统美食、民俗表演......共同编织成一场荆楚文化的绚丽画面。”文化扶贫在行动采访团走进湖北民俗民艺第一村——莫愁村,感受荆楚文化魅力,见证文旅融合发展的“钟祥样本”。千百年来,围绕莫愁村、莫愁女,以及“阳春白雪”和阳春台、白雪楼等传诵着许多动人故事、为历代文人墨客所倾慕寻访。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来源: 荆楚网
雕刻时光(大地风华·走进古村落)
王剑冰
一
鸟儿铺满天。朝阳的金轮滚滚而出。
这个时候,你会听到一处处门窗开启,听到或清脆或沉郁的声声诵读。更多地,听到刻刀在木板上的雕琢声,坚实而有力,雕刻的汉字渐渐凸显。你还会听到墨刷匀称细致地走动,纸张掀开,一篇文字清晰地呈现。
有人在锯木。大木头截成板材,板材截成小板。刺啦的响声中,木香喷溅。
事实上,一个个院落里、屋檐下、廊径旁,很多匠人在同时操作。
高台上的铁匠铺,年轻的徒弟赤膊上阵,大锤抡得正圆。老师傅一丝不苟,小锤叮叮当当,铁砧上的物件火星四射。淬火的一瞬,才看清,那是一件精致的雕刀。
声响合在一起,合成竹桥村的铿锵乐音。时光似乎没有远去,声音留在了竹桥村的门廊墙缝间、天井花池中。
明清之际,江西抚州的金溪曾是赣版书籍印刷中心,有“临川才子金溪书”的美誉。临川才子晏殊、曾巩、王安石、汤显祖可谓名闻宇内。金溪与临川山水相连,明代成为赣东商业重镇,并向书业、纸业发展。到清嘉庆年间,竹桥人余钟祥在浒湾镇创办了“余大文堂”刻书房,成为金溪最大的刻书房。纸张掀动,书板盈架,刻印之声盈耳,车马船只不断。由此带动了浒湾和竹桥,使其成为“金溪书”的发祥地和主要承印地。
现在竹桥村留存的“养正山房”,当年也是一个刻印古籍的地方。它位于仲和公祠的右侧,里面庭院广大,上堂及后堂都是印书之所,各类人等操忙其中。
竹桥是精致典雅的。它就像一帧古典的扇面,展开在青山绿水间。你看,扇面上是一个个门楼、一座座祠堂、一处处庭院,其间,有蓊郁的古树和盛开的花草。古老的宅院大门开启的一刻,连空气都透着幽香。
幽香中,袒露着木版、刻刀、磨刷,袒露着长桌、纸张、书籍。
村边蜿蜒而过的古驿道,多少车轮滚动,多少马蹄声声。古驿道仿佛竹桥的金腰带。有了它,竹桥多少年都意气风发、神采飞扬。
青山不老,碧水长流。现在,竹桥村还有《三字经》《百家姓》《四书集注》的雕版,不少线装古籍仍可在这里印刷装订。
竹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中国传统村落标本。
二
知道竹桥人大都姓余,却不知道他们大多数人的名字。他们留给我的,是一个群体性的概念:讲究风俗,讲究传承,讲究文化,求的是“五谷丰登”“天地祥和”“勤俭持家”“以人为本”。
村中,每一处建筑、每一块雕刻,竹桥人都有说法。譬如,村头的井凿成方形,三口井形成“品”字,寓意村人无论贫富贵贱、求学经商,都要恪守品德。
进出的门楼,前后通道用石条铺设成“人”字形、“本”字状,寓意无论居家还是在外,都应以人为重,不能忘本,提示着老祖宗永远的教诲和期望。
连池塘也有规矩。八个池塘,中间一塘呈月形,形成“七星伴月”之象。池塘将村子连缀起来,从不干涸,从不漫溢,滋润着春夏秋冬的岁月。
竹子生长在村子的周围、老宅的前后。“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即我师。”竹桥人的淡雅通透可见一斑。村民之间诚挚相待,一家有事,他家相助。
文明的种子代代传续。厅堂、廊道、立石,到处可见名言警句:“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这是对生命的提醒,也是精神的激励。
祠堂里,放着绣球、长龙,放着乐鼓、雄狮。到了节日时,村中的一条条巷子都热闹欢动。地域文化特有的氛围,连外边的人来,都不由得融入其中。
在这雕版印制之地,过去,女子也要会刻字、印刷,所以从小就在学堂认字读书。从这里出去的女子,个个灵巧。不惟女红出彩,更是知书识礼、聪明睿智。
由于有着良好的读书氛围和文化环境,抗战时期,金溪中学的课桌就放在这里。琅琅读书声在青山绿水间、祠堂庭院里回荡,弦歌不辍,文教之风赓续。
三
一位老人靠着老宅打盹,旁边,一箩箩红辣椒,红红地缠绕着他的梦。
听到脚步声,老人从梦里醒来。问他,可是这座老宅的主人?老人笑着称“是”,并邀请我入内。先是一个天井院,而后一个大厅,厅里挂着楹联:瑞日芝兰光甲第,春风棠棣振家声。奇妙的是,天窗还有滑道,可以拉上滑开。底下的水池,也有明槽,加盖石板,可举行大场面活动。
老人说,他小的时候,喜欢跟小伙伴一起捉迷藏,村里的巷子多,祠堂也多,藏在哪里还真不好找。
顺着溪水转去,窄窄的巷子里,一对年轻人拉着手跑过,笑声自他们身后传来。后来在一处名为“苍岚山房”的老宅,又遇见了他们。苍岚山房曾经也是学子读书的学堂。原来,男孩是带着女友来村里祖宅玩。女孩十分喜欢竹桥村,在村中跑来跑去,转了半天,还没有转完。
年轻人喜欢这里,多半是因为那文脉相传的意蕴。你看,一处雕着“谏草传芳”的老宅,门上贴着“天赐良缘”的新对联,似刚刚举行过一场婚礼。
一位彭姓女子,在老宅门前卖萱草膏。她是双塘镇人,老宅是夫家的。孩子上了大学,自己闲着没事,就着老宅做些小生意。
导游小饶也是外村人,嫁到竹桥的余家。竹桥的文化感染了她,慢慢地她做起了导游。讲说时,她恨不得把知道的都告诉游客,且常常露出自豪的神情。
远处的钟声,一层层的,把黄昏覆上了黄铜的颜色。群鸭正顺着溪水回家。
马上要到抢收抢种的时节了。村子周围,早稻扬着金色的穗子。水田里,还有人在忙着培植晚稻。
入夜,凉风忽作,将燥热吹去。遂有雨落,淅淅沥沥敲打着竹桥的层层瓦片,敲打着苎麻、苦槠和香樟……
悲情“水都”丹江口:贫困县居民一生都在搬迁
丹江口市被当地官员称为“中国最悲情的城市”。
10月26日上午8时,丹江口水库水位160.5米,湖北丹江口市均县镇老镇三面已被上涨的水包围。因移民安置未谈妥,55岁的均县镇居民明瑞香仍留守在老镇的房屋内。近两年前,均县镇已整体搬迁至6公里外的新镇。
明瑞香已不是第一次面临移民搬迁。1966年,7岁的她随父母从均县(今丹江口市)肖川乡老家搬离。家离县城不远,她仍记得县城高大的城墙,县城搬迁时,触摸到城砖中的古代黏合剂中有糯米。
明瑞香已不记得当年搬过多少次家。因不知道水库最终淹没线水位,搬到一个地方临时搭建屋棚后不久,水位又涨了上来,不得不再次搬迁,直到搬到均县镇老镇所在的关门岩村定居。
12月12日,南水北调中线正式通水,丹江水一路北上。通水前夕,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探访核心水源区湖北十堰丹江口市。丹江口因为南水北调后向北方供水,给自己起了一个“水都”的名号。这座城市半个世纪历经两次大规模移民。第一次,丹江口大坝修建,两千年的老县城均州古城永沉水底。第二次,大坝加高,淹没水位线上升,为纪念均州古城而命名的均县镇,整体搬迁,剩下一片废墟。丹江口为南水北调牺牲太多,也因此,被当地官员称为“中国最悲情的城市”。
与水告别
10月26日上午,45岁的蒋德成和两个儿子、不到一岁的孙子开车回均县镇老镇住处。快到集镇时,车在一处房屋前停下,父子两从尾箱抬出一台电瓶,进入屋内,换上另一台充满电的电瓶抬进尾箱。
这里是老镇的两个冷库之一,也是至今仅有的两处没停电的地方。2012年12月30日,老镇整体搬迁至6公里外的新镇。2014年大年初六,老镇停水停电,大半年来照明只能靠太阳能和电瓶。
“(一台电瓶)照明看电视能用半个月,用冰箱的话两天就用完了”,蒋德成一家刚从新镇买菜回来,大约每隔4天去买一次菜。
蒋德成是渔民,世代打渔为生,1958年丹江口大坝修建前,爷爷在大坝以下汉江河段打渔,大坝建成后,父亲和他一直在均县镇附近水域打渔,这一带水面宽阔,属回水湾,水较平,便于停靠。
10多年前,蒋德成和其他渔民开始网箱养鱼。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在岸上租房子住,之前很多年里一直住船上。两年前集镇整体搬迁前,他租住的房屋因在淹没水位线以下,被拆掉,集镇整体搬走后,他便选了一处原粮站的空房住了进来。
集镇迁走后,人去楼空,只剩下渔民和少部分住户,很多房屋的门窗被敲掉,院内长满杂草,街道凹凸不平,街景像地震后一般。
网箱养鱼并不忙,早晚投饵各两小时,“自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余时间,蒋德成会到街上小卖部打牌,可最近因为人少,“经常凑不满一桌”。
蒋德成家养了100多箱鱼,主要是丹江口的地理标志产品鳡鱼和翘嘴鲌,每年投喂饲料几百吨,为防鱼病还要喂药。“水库里的水流动性强,比池塘里养鱼喂药要多十倍”,蒋德成告诉澎湃新闻,南水北调通水在即,因饲料和鱼药给水体带来污染,政府已开始着手取缔网箱养鱼,到2015年12月30日前全面取缔。
以前除了养鱼,蒋德成还在自家水泥趸船上卖饲料,可最近养鱼的人减少,几乎没人买饲料了。尽管近两年市场不景气,鱼价下跌,养鱼赚的钱只够养家糊口,“算是自己给自己打工”,但蒋德成还是喜欢养鱼的清闲与自由。
明年底把最后一批鱼卖掉后,蒋德成打算重操旧业打渔。不过打渔要比养鱼辛苦得多,每天深夜要去放网,清晨收网,成天泡在水里。
网箱养殖是丹江口库区的主要产业之一。丹江口市官方向澎湃新闻提供的数据显示,该市有网箱养鱼12万箱,年产值6.8亿元。
蒋德成家不养鱼后,家里不再需要那么多人手,为了将来让孙子在城里接受更好的教育,儿子蒋刚、儿媳饶霞将会去丹江口城区生活,离开水边的生活。
一生都在搬家
饶霞去年嫁入蒋家,她本是大坝加高后外迁的移民,4年前随父母迁往湖北宜城市,在那边过得还不错,“种西瓜和棉花”。
饶霞的娘家原在均县镇老龙沟村,位于丹江口库区一处湖叉上方,部分属淹没区。村民可根据意愿选择是否搬迁,大部分村民选择了外迁。饶霞对澎湃新闻说,“我父母等搬迁已经等了20年,从我没出生就开始等起”。
丹江口市官方提供给澎湃新闻的资料显示,从1991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开始核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淹没实物指标开始,库区就停滞了发展。老龙沟村地处深山,没通公路,生活条件艰苦,当地居民急切盼望搬迁。
2010年的一天,饶霞家的家什先是用船从村旁水库运到老集镇货运码头,然后由政府安排的货车运往宜城。
她没想到自己3年后又会回来。当地也有人上门做媒,可她选择了丈夫蒋刚,两人是初中同学,“别人有钱,没感情最后还是过不好,不如我们有感情基础的”。
而另一些人,离开这片土地时却是另一番滋味。均县镇关门岩村的李本秀老太太,随儿子搬离家乡时“哭得好狠”,李在离开前已查出患癌症,第二年去世。
在丹江口,移民故事俯拾皆是。有人丹江口大坝修建时就开始搬迁,流离颠沛返乡,4年前,大坝加高时又不得不搬离,一生都在搬家。
丹江口市官方提供给澎湃新闻的材料显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丹江口水库前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移民。1958年丹江口大坝开始修建后,移民即已开始。2005年,为保证南水北调供水,大坝从162米加高到176.6米,水位上升带来新淹没区,由此进行第二次移民,从2009年开始。该市库区1960年代第一次大规模移民16万人,此次大坝加高移民近10万人。
丹江口市新闻中心副主任陈华平告诉澎湃新闻,该市浪河镇浪河口村村民何胜友因为南水北调,一生搬迁达6次。1967年丹江口大坝下闸蓄水后,因不愿迁走,何胜友家中被上涨的水淹,天亮后看到没顶的房子,“有无数条蛇和老鼠爬在上头”。
陈华平向澎湃新闻介绍,河南淅川县的2万多移民迁往海拔3000多米的青海省,因和当地居民发生械斗、高原反应、饿死等原因死亡的人数达三分之一,最后只有“双脚跑回”,改迁湖北钟祥市大柴湖,在那里的芦苇荡里开荒种地,现已发展到7万多人,却“至少落后老家20年”。
“水中有多少丹江口人的眼泪和心血”
即使那些就近搬迁的人,所谓内安或后靠移民,也有自己的困扰。
距均县镇老镇2公里,一大片新盖楼房,是关门岩村移民安置点。49岁的张国云,以前在老镇学校附近居住,家里的房子出租每年有2000元收入,孙子上学近,可以在家里吃饭,买东西方便。
自从搬到移民新村后,村民生活不便。移民新村距新镇4公里,两地之间交通靠坐中巴车,每趟车费5元,村里没菜市场,“买菜要花10元钱车费”。半个月前,开通了2元一趟的电瓶车,才为村民省出部分车费。
“每天早上六点钟就要起床,给孙子做饭,六点半送他去新镇的学校上学,每月要交500元生活费。”张国云家有7亩桔园,到桔园劳作极不方便,得步行2公里。
张国云等多名关门岩村村民告诉澎湃新闻,该村搬迁快2年,每户8000元的房屋维修基金、每人5000元的养老金、每人每年600元的移民搬迁后续生活补助,至今未发放到位。
受移民工程影响的还有当地干部。南水北调中线移民开始时,河南省提出“四年任务,两年完成”,湖北省则提出“四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三年彻底扫尾”。
如此一来,给当地干部带来巨大压力。当地干部为了动员民众搬迁,日以继夜、挖空心思工作。
均县镇副科级干事张飞告诉澎湃新闻,干部上门动员移民或拆迁,很多当地居民常躲着故意不见,有的干部为了做老百姓工作,主动上门为对方干家务、收割、种地。
丹江口市官方提供给澎湃新闻的一份材料称,4年间,该县仅牺牲在移民工作岗位上的干部就有6人。
陈华平对澎湃新闻抱怨,丹江口大坝2005年就开始加高,直到4年后才开始移民,“国家为什么不早点启动库区移民搬迁?这样工作也可做细一点儿。”由于移民时间紧,政府为移民修建的安置房施工时间大大缩短,为了赶工期,往往得牺牲房屋的建筑质量,陈华平告诉澎湃新闻,房屋质量成了移民上访最常见的原因。
陈华平介绍,该市一位女干部参与移民工作期间历经被狗咬、流产等痛苦,在QQ空间写道:“南水北调是众所周知的国家工程,当有一天,北方人民品尝到清甜的丹江水时,他们可知道这些水是经历了怎样的艰辛才从丹江口流到北京的?这一滴一滴的水中,有多少移民和移民干部的眼泪和心血?”
均州往事
半个多世纪前,丹江口就开始为南水北调让路,命运随之而变。
1965年冬天,父亲带11岁的丁力先去看建设中的丹江口大坝,坐帆船溯江而上,看到已被拆毁的均州古城剩下的半边高大城墙,城里没人。那是丁力先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淹没前的均州古城。一路上父亲一言不发,若干年后,他才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
丹江口市南水北调办原副主任丁力先的家原在均州古城内,是城中望族,1949年后家道中落,父亲到乡下教书,全家搬往大山里生活。
1967年丹江口大坝下闸蓄水,古城永沉水底。像丁力先一样,很多丹江口人每每提到这座古城,言语间总是充满怀念与惋惜。
丹江口市前身为均县,中国道教的发源地,道教创始人净乐国王子玄武出家修行的地方,如今已鲜为人知。
明朝初年,为了供奉真武(即玄武)大帝,永乐皇帝大修武当山,建皇家道观,在均县县城修建了供皇帝上山前净身及物资中转的净乐宫,为武当山八大宫之首。
10月27日,72岁的张国光陪媒体拍纪录片来均县镇,寻找消逝的均州古城。张国光在古城生活过近20年,费时6年,画了一幅8米长还原均州古城的画。
均州古城位于今丹江口市城区40多公里上游的汉江边。县城以上水面较窄,以下水面较宽,自古以来是上下游货物集散地,还是朝拜武当山的停靠点。
张国光曾经的家在县城正街南大街。“我家门口经常路过’朝武当’的人”,直到张国光儿时,当年盛况还在延续。张国光记得,城外汉江边码头一天到晚“人来人往,非常繁忙”。南下的山货,北上的南货,都在此下货中转。码头对面有一条街叫朝武街,朝拜武当山的人多在此歇脚,有香、纸等各色商品。
货物集散和朝拜武当的人停留,给均州古城带来繁荣。最令张国光印象深刻的,还是净乐宫和古城墙。净乐宫占地面积约5万平米,约占古城一半,城中大道一头直通武当山,另一头通入净乐宫。城内均为青石板铺就。
张国光小时候经常到净乐宫游玩,攀爬里面一块巨石雕成的乌龟,龟旁石碑上刻有修建净乐宫时皇帝下的圣旨。
在张国光的记忆里,均州古城城墙尤其宏伟,胜过现存的襄阳古城墙。民间有“铁打的均州府”的说法,称其城墙长3.5公里。
1958年,丹江口大坝开始修建,为避免截流后运输不便,县城开始搬迁。当时县城居民约2万人。居民们徒手将房砖、木料、家具等搬离,城墙被拆了一半。
净乐宫只搬走了一对石龟、一个牌坊,迁至今丹江口城区,放在复建的净乐宫内,其余500余年的建筑皆毁弃。
县城搬迁用了不到两年,均州古城成了一座空城,整体迁至今丹江口城区。
城外嚣川区(后更名肖川乡)后靠搬至均县镇老镇所在地,为纪念水下那座永远消逝的古城,肖川乡更名均县镇。没想到20年后,均县镇再次整体搬迁。
“悲情城市”
大坝的修建,也改变了丹江口人的命运。除了一生没完没了的搬迁、移民,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受到因修水库带来的种种影响。
丁力先告诉澎湃新闻,该市耕地被大量淹没,人均耕地面积由1.12亩下降到0.32亩。被砍伐的森林面积达25万亩,“大树被砍光”,至今很多地方仍受“地球癌症”石漠化困扰。境内被水库分割为江南、江北,交通阻隔。
更让丁力先不吐不快的是,近年来各地变化日新月异,很多事物“从无到有”,而丹江口市却是“从有到无”。为了修建丹江口水库,该市1966年就修通了到汉口的铁路,可这条铁路至今只是断头路,从12年前就停开了客运火车。襄渝铁路复线修建时,该市力争该铁路从丹江口过,未果。
至今仍无高速公路途径丹江口城区,这里成了交通“死角”。澎湃新闻记者在丹江口采访时注意到,从丹江口去周边中心城市火车站、机场,包括其所属的十堰市,皆在两小时以上。丁力先向澎湃新闻透露,北京某女演员来丹江口拍一部南水北调题材电影,走时赶飞机误机,埋怨“你们这的交通也太差了”。
更让不少丹江口人耿耿于怀的是,1994年,该市举全市之力,将境内为数不多未被水淹的旅游资源武当山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可10年后,武当山的管辖权却被从丹江口市划走,设立了武当山旅游特区,属十堰市管辖。这被称为“丹江口市人民心头永远的痛”。
10月23日,丹江口市环保局副局长魏庆九向澎湃新闻介绍,丹江口市99%以上的国土面积在库区,2000年以后,为支持南水北调调水,保护丹江口水库水质,该市关停了大量污染企业,工厂所剩无几。
“我们现在引进的企业,首先要过环保这一关,不合格的坚决不要”,魏庆九告诉澎湃新闻,该市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环保不过关将影响官员升迁、评优,这是保水质的“政治任务”。
魏庆九介绍,为保护水质,该市今明两年将取缔库区内所有网箱养鱼。“为了一江清水北送,我们把自己最传统的产业都牺牲掉了”。
由于丹江口在南水北调中作出的牺牲,自身发展困难重重,至今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当地有人戏称“全中国叫‘市’的国家级贫困县有多少?”,陈华平则将其称为“中国最悲情的城市”。
“我们为南水北调付出了这么多,得到什么呢?”丁力先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