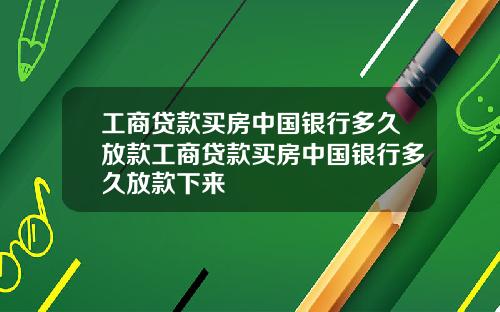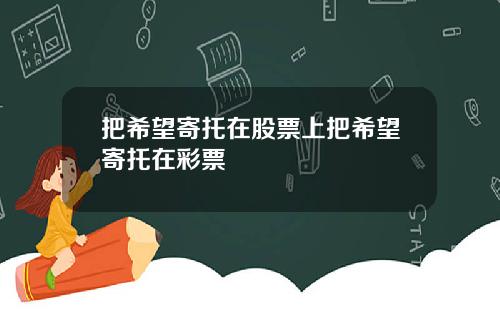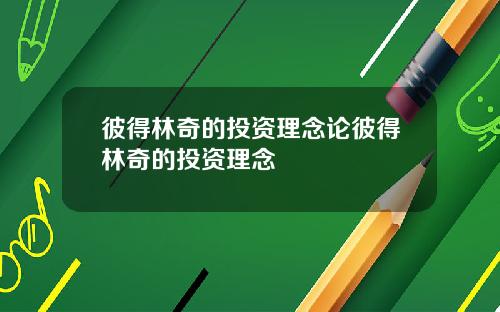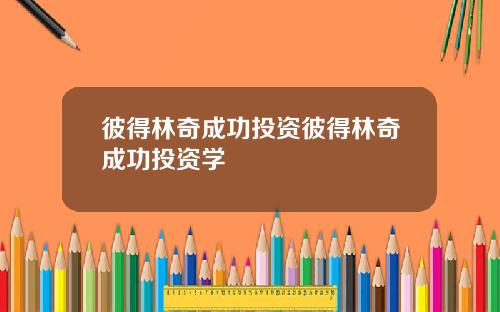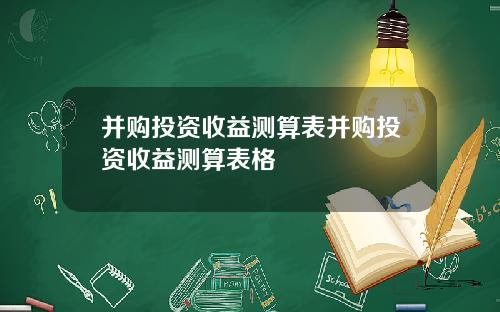金石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文章目录:
1、天安门城楼伟人画像有八个版本(下)2、“哦,这就是鲁迅”:108岁的马识途回忆文坛名家3、福建省柘荣一中赴新西兰开展教育与文化交流
天安门城楼伟人画像有八个版本(下)
天安门城楼先后悬挂了八版伟人画像。北平和平解放大会,伟人画像第一次悬挂在天安门城楼。随后的“五一”“五四”及北平市各界人民纪念抗战十二周年暨庆祝新政协会议筹备会成立大会上,天安门城楼都高悬伟人画像。“开国大典”上,伟人头戴八角帽的巨幅画像悬挂在城楼正中。第二年,第一张免冠画像短暂悬挂后,以伟人第一张标准像为摹本的画像挂上城楼,迎接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节。其后,以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标准像为摹本的画像挂上城楼。
以第一版标准像为摹本的画像挂上天安门
1950年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中央新闻总署副署长兼新闻摄影局局长萨空了向胡乔木建议,由新闻摄影局专门为毛主席拍摄一张正式的标准像,向国内外发行。这样不仅能保证国内许多重要场所和会议上悬挂毛主席像的标准一致,同时也在国际上树立毛主席的新形象。
△毛泽东主席第一版标准像。
拍标准像最好到照相馆去拍摄,因为照相馆里的灯光照明条件好。但在新旧政权更迭之初,国内局势复杂,出于安全考虑,毛主席不能外出到照相馆拍摄照片,为此中央决定由新闻局派摄影师到中南海为毛主席拍标准照。
中央新闻局经过研究,派出了齐观山、陈正青、郑景康、侯波四位摄影记者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所。毛主席政务繁忙,只能抽出一个小时拍摄。由于时间仓促,加之光线等客观条件的原因,4位摄影师拍出的照片都不是很理想。
这次拍摄可谓“出师不利”。怎么办?萨空了把陈正青找来商量,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在摄影局找一位摄影后期加工制作技术顶尖的同志,从毛泽东现有的照片资料中挑选并制作出一张毛主席标准像。
“陈石林同志能担当此任。”陈正青向萨空了建议道。萨空了当即拍板:“对,让陈石林来制作毛主席标准像。”
陈石林何许人?为什么萨空了和陈正青两人都倾向由他来制作毛主席第一张标准像?
陈石林1929年出生于江苏扬州,曾就读扬州中学,后因国事纷乱家境贫寒,不得不中途辍学。15岁时,他在扬州的一家照相馆里打工。在这里“偷艺”学会了冲洗胶卷、修片等技术。他带着“偷”学来的技术,先后来到南京国际艺术人像摄影公司和香港大光明电影公司深造。在这里他有幸接触到了欧阳予倩、高岭梅、赵家禹、舒绣文、顾而已等摄影界、电影界名流。在香港,陈石林不仅提高了摄影技术,还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1949年,年仅20岁的陈石林就担任了台北市国际艺术人像公司工作部主任,与我国摄影界泰斗郎静山先生一起共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正是用人之时。陈石林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假道香港回京。在香港滞留期间,他从电影艺术家欧阳予倩那里得到一张由徐肖冰拍摄的毛泽东和朱德在延安窑洞一起研究作战计划的电影拷贝。这张电影拷贝让陈石林激动不已,因为在香港还没有一张毛主席像。陈石林要用这一电影拷贝制作出一批毛主席像在香港发行,让香港同胞一睹毛主席的风采,也算是向新中国诞生献上的礼物。
冲动即刻变成行动,陈石林和大光明电影公司的两位同事沈克定、盛家骥合作,开始了毛主席像的制作:修改,翻拍,再修改,制成负片后再冲洗放大,一批层次丰富、画面清晰的照片被制作出来。照片随后被分批送到香港九龙的各家书店,很快售罄。这次制作,不仅让陈石林向新中国献上了一份贺礼,同时也为他后来制作毛主席标准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陈石林到北京后,分配到中央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从事修版等技术工作。当新闻摄影局将制作毛主席第一张标准像的重任交给他,他在激动和自豪的同时,也感到巨大的压力。要制作出能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展示的毛泽东标准像,既需要真功夫,更需要对毛泽东的了解,为此,陈石林扎进了资料图库,把所有与毛泽东相关的工作照、生活照、团体照、个人照全都看了一遍,然后精挑细选。再将精选出来的照片,一张张地进行揣摩和研读。
最终,陈石林将目光定格在1950年6月毛泽东主席与部分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的合影照上,其由陈正青拍摄。拿着这张照片,陈石林向局领导汇报。经局领导同意后,陈石林便开始了加工制作。
△1950年6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毛主席第一版标准像即从这张合影中“抠”出来的。
陈石林首先将这张合影中的毛泽东主席单人像从其第三颗纽扣以上进行裁剪,放大成12英寸照片,然后将毛泽东主席左侧后面的人头像修去,再对毛泽东主席像的面部、头发、衣服等处加工修饰。在制作中,为了能突出毛泽东像面部影调的层次,陈石林选用了几种不同反差的相纸,运用遮光技法,制作出十多张不同反差的12英寸照片。在反复比较中,选出了一张面部光影层次丰富、布幕背景明亮的照片,翻拍成6×4.5厘米的底片,放大成标准照。这张毛泽东主席标准像,形象大方,和蔼可亲而又不失庄严。有关领导阅后非常满意,经毛主席审阅同意后,新华社很快就向国内外公开发稿,同时大批量洗印。
当年印刷发行的毛泽东第一版标准照达2000多万幅,发行到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新中国成立50周年发行的新版百元人民币,2000年10月发行的20元面值的人民币,它们正面毛泽东头像,都是以这第一版毛泽东标准像为摹本雕刻成凹版印出来的。
与此同时,参与毛主席画像任务的画家们,便以毛主席第一张标准像为摹本,绘制出第五版毛主席画像,于1950年国庆前夕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幅毛主席画像的绘制者仍是辛莽、左辉、张松鹤等人。
伟人画像的再次变换
1951年春,为了配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出版,中央决定再制作一幅毛泽东正面的标准画像。
陈石林和新闻摄影局的同志一起翻阅了成千上万张照片,终于从一卷用摇头转镜相机拍摄的团体合影中,找到了一幅适合制作标准像的毛泽东正面形象。但是,这张照片是用美国制造的7英寸宽的黑白航空胶片拍的,照片反差过大,影调层次欠佳,再用简单的遮挡放大技术是不行了。陈石林大胆采用绘画主义摄影派的表现手法,将毛泽东的头像从合影中单独剪裁出来,放大成12英寸的照片,然后用刮刀在不损伤相纸纸基的基础上把药膜面上的黑色背景一点点刮掉,再将毛泽东面部精心修整,并更换了浅色背景后,将一幅和蔼可亲、气宇轩昂的毛泽东正面标准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1952年毛泽东主席第二版标准像。
这幅照片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认可和毛泽东本人的赞许。随即,毛主席第二版标准像开始大量洗印并发往全国,同时,以这张标准像为摹本绘制的毛主席画像于1952年国庆节前夕被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这次绘制毛主席画像的有张振仕、王其智、金石、陈永贵等。这次画像,按时间为序,是第六版被悬挂在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画像。
1959年,为了迎接国庆10周年,需要更新毛主席的标准像。这项任务交给了新华社摄影部中央新闻组资深记者孟庆彪和新华社驻中南海记者侯波同志。他们事先在毛泽东住处附近布置了一间摄影室,安置好灯光,测试了各种不同的光线和曝光指数,趁毛泽东开会的空隙时间,拍摄了第三版毛主席的标准像。但由于受客观条件限制,两位摄影师拍摄了两个胶卷的底片,却没有一张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负责摄影的侯波同志请了四位照相馆高级技师进行加工修整同一画面,每人修一张,共四幅照片,他们修得都很细、很均匀,但经翻版放大出的样片难以令人满意。在这种情况下,编辑部的同志要陈石林修整一幅供领导评比。
陈石林事后回忆说:
我首先自创复制底片,然后在复制底片上修整,去掉画面背景上的灯罩投影,衣服上多处皱褶,修齐了衬衣领,减少强光部位密度,增加暗部密度,控制好复制底片的密度差。对面部皮肤、面额,每动一笔都要从政治人像的真实性考虑,直接用复制底片放大出皮肤润泽、柔和而有质感的样片,和照相馆高级技师修整的四幅样片,一同送中央审批。经过评选,选用了我加工的照片,作为侧面标准像向全国发稿。
毛主席标准像向全国公布后,画家们便依这幅毛主席标准像绘制天安门上悬挂的毛主席画像。这次的毛主席画像绘制,以画家张振仕为主,金石、陈永贵、王其智等画家配合。经过画家们的努力,以第三版毛主席标准像绘制的毛主席画像于1963年9月30日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3年毛泽东主席第三版标准像。
由于画家张振仕当时年已半百,体力已难以承受大负荷的劳作,天安门管理处便将绘制毛主席画像的任务交给北京市美术公司来独立承担。从1964年开始,美术公司分配王国栋、陈永贵、金石三人来绘制天安门城楼伟人画像,王国栋为负责人。
王国栋以毛泽东主席标准像为摹本,注重对毛泽东主席眉宇和眼神的表现,力求在描绘毛主席慈祥和善的同时,表现出他的性格中敏锐、机智和洞察一切的特点,通过毛主席的眼神,表现毛主席的内在气质。王国栋认为绘像应力求准确,尽量求真,使人们在看到画像的同时,想起毛泽东主席的丰功伟绩,感受到他的伟大,更生崇敬之情,一切绘画的技巧都应服务于此。
王国栋特别注意兼收并蓄,吸取他人之长。在掌握民族画法的基础上,他虚心向学习西洋画法的公司同行陈永贵请教。因此,王国栋在绘制巨像中,既能准确地掌握人物的轮廓,又能以中国老百姓可接受的方式着色,使他画的毛主席油画像更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为了画好毛主席画像,王国栋、陈永贵、金石等人还想出了一些独特办法:由于画像巨大(一只眼睛、一张嘴就有一米多长),画家们要不断从各种距离观看自己的作品。为了把握好效果,他们把本应是放大的望远镜倒过来,从近距离缩小巨像的局部。一边画像一边用余光扫视附近的红墙,使画像上毛主席的气色能与天安门城楼的红色相配;如果近看,毛主席面色很红,也极为立体,但放在城楼上,就与周围环境十分协调。
在画像的背后即画框的龙骨上加一层铝合板,然后再加上五合板。绷上画布,可以使雨水顺着铝合金板流下,从而保证了画像在较长时间内不变色。这是王国栋在绘制毛主席画像时的经验总结。
△1967年毛泽东主席第四版标准像。
在最初,绘制毛主席画像所用的画布,是三块画布拼接在一起的。因接缝不平,画面上两道直贯上下的棱子十分显眼,影响肖像面容的美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天安门管理处派人到哈尔滨亚麻厂求援,要求生产出适合用于绘制毛主席画像用的整幅布料。但亚麻厂的织机的宽度不够,管理处又找到天津地毯厂。两厂合作攻关,终于试织出密度不同的几种宽幅亚麻布。王国栋亲自去工厂,选定了一种,当时织出的亚麻布足够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各用十年。后来人民大会堂改挂国徽,几百米亚麻布就统归天安门使用。新织布约五米宽,正好是画像的宽度。
群众出自对毛主席的热爱,对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半侧面标准像提出意见建议,比如毛主席画像只突出左耳朵,且左眼珠偏上,显得不庄重。于是中央决定要赶制一张两耳全露的正面标准像。陈石林再显真功,毛泽东第四版标准像公布。画家王国栋根据这一版标准像,精心绘制出巨幅毛主席画像,于1967年国庆前夕,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这是自1949年天安门悬挂第一个版本毛主席像后的第八个版本,也是画家们根据第四版毛主席标准像绘制的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
伟人画像的秘闻
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画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期,不是每天都悬挂。通常是每年五一、十一,悬挂画像10天左右。从1966年8月18日开始,天安门城楼每天都悬挂毛泽东主席画像。
唯一的特例是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在举国追悼的日子里,天安门城楼换上了新华社用翻正翻底法制作的毛主席巨幅黑白照片,追悼会后仍悬挂王国栋画的画像。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王国栋的徒弟葛小光在1977年接继开始绘制毛泽东主席画像后,力求通过对毛泽东主席眼神的刻画,表现出一代伟人深邃的思想和博大的胸襟,并力图通过这双眼睛,在领袖与人民、历史与现实甚至未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画像时,葛小光总是在寻求一种“感觉”,这种“感觉”难以表述,但也正是这种感觉恰好完成了他所追求的神似。正如许多人在天安门城楼前仰视毛主席画像时,都会说出同一句话:“真像!”也正是画家炉火纯青的画技,从而达到了这种效果:站在天安门广场,面向天安门城楼,无论怎样变换位置,都会感觉毛主席在用慈祥的目光注视着你。
△每年国庆节前,都要更换一幅新的毛主席画像。
有人会问,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主席画像为什么不挂照片。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的画像是一年一换的,一年中,要经受风吹、日晒、雨打,挂上去时与取下来时色彩相差不能太大,因此,制作时也就特别讲究,着色时太淡不好,太深也不行。照片存在角度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只能如实反映,最多只能修修版。画像则不同,画本身把伟人的形象给理解化了,通过各种角度的照片考证、验证,观察,在画家的脑子里形成一个立体的形象,这样在绘画时就把照片上精到之处得到保留,照片在摄影上弥补不了的,绘画时都可以克服。这就是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画像不通过照片而运用绘画手法制作的原因。
1994年前的毛主席画像板由21块五合板和铝板制成,不仅易变形翘角,而且影响画像的整体效果。1994年,为迎接国庆45周年,在大规模粉刷、装饰天安门城楼的同时,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也进行了更换。更换后的画板为一整块采用新工艺研制而成的平面玻璃钢,弥补了以前的不足,增强了画像的效果,使毛主席画像更加光彩夺目。
(本文作者朱彦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民盟盟员、陕西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特约研究员,闫树军为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哦,这就是鲁迅”:108岁的马识途回忆文坛名家
《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作者:马识途,版本:人民出版社 2022年1月
看到鲁迅
对于鲁迅,我是看到过的,我说的是看到过的,不是说见到过的。像鲁迅这样的大文豪,在他去世前,我还不过是一个中学生,怎么可能和他相见过呢?但是我的确看到过他,而且有两次,我终生难忘。1932年,我在北平大学附高中上学,那个学校的校长是留学法国回来的教授,主张自由平等博爱那一套,所以民主风气比较浓厚,有许多思想进步的同学,同班有一个叫张什么的同学就是一个。有一天他约我出去听一个讲演会,我问他谁的讲演,他说去了就知道。我们到了和平门外师范大学的大操场上。他才告诉我说是一场秘密集会,而且主要是听鲁迅的讲演。我能被秘密通知来听鲁迅讲演,我也算是进步分子了,我很高兴,还有点得意。
不多一会儿,看见一个个儿不高比较瘦的半大老头登上桌子,没有人介绍,也没有客套话,就开始讲起来。哦,这就是鲁迅!鲁迅讲了些什么,他那个腔调我听不清楚,我似乎也不想听清楚,能第一次看到鲁迅,而且在这种场合看到鲁迅,也就够了。不多一阵,鲁迅讲完,忽然就从桌上下去,消逝得没有踪影。我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讲完的。人群纷纷散去,我们也回平大附中去了。
在路上,张同学才对我详细地讲关于鲁迅的情况。他说,鲁迅是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中国新文化的领军人物,同情中国革命。反动派特别忌恨他,所以这次他是秘密到北平作讲演,知道的人不多,你不要告诉别人。我说:“我在初中时就读过鲁迅的《狂人日记》,很崇拜他。你约我去,让我看到了鲁迅,我很高兴。”从此,我就成为他们进步分子的一员了。
初识汪曾祺
我和汪曾祺认识是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那正是抗战时期。我和他都是中文系的学生。他高我一年级。有一次,中文系出一个通告,那种别有风味的书法,引起我这个爱好书法者的注意。我问同学,这是谁写的?同学告诉我说,是汪曾祺写的。汪曾祺是谁?同学回答,是我们系里的一个才子。他写得一手好字,更写得一手好散文,颇得朱自清、沈从文教授的赏识,是沈从文的及门弟子,其貌不扬,却为人潇洒。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汪曾祺这个同学。后来由于西南联大实行的是学分制,我和他虽不同年级,却同时选了沈从文先生的文学创作课和闻一多先生的“楚辞”“唐诗”几门课,于是在课堂上就认识了。但是相交淡若水,没有多少来往。
那时我看过他写的字,也读过他发表的散文,觉得都很出色。他的散文淡雅清丽,读来别有情趣。从艺术上说,很有特色。我也听说沈从文说过他自己的散文赶不上汪曾祺,还听说过汪曾祺为人捉刀写论文(当时以交一篇论文或作品作为期末考试卷),交到闻一多先生那里,闻先生看了说,这篇论文比汪曾祺交的论文还写得好一些。有这样的事情,可见他也受闻先生的赏识。
那时我们认识,我却未想和他来往,就因为他是一个潇洒的才子。我尊重他是我们中文系的一个才子,从艺术上我也欣赏他的散文,但是我并不赏识他的散文那种脱离抗战实际的倾向,特别是他们那一些才子过的潇洒生活,也就是睡懒觉,泡茶馆,打桥牌,抽烟喝酒,读书论文,吟诗作词,名士风流。这时正当抗战时期,这种玩世态度和潇洒生活,就为学校的进步同学所诟病。不说他们醉生梦死,也是政治上不求进步的吧。我则认为他们爱国上进之心是有的,认真钻研专业是可取的,政治上居于中间状态,是我们争取团结的对象。事实上他们后来都卷入到学生运动中来了。汪曾祺就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
闻一多先生无奈刻图章
闻一多先生学识渊博,诗书画印,无不谙熟,加上他早年学艺术,中年攻古文,对于甲骨、金石、篆刻一类的功夫,造诣很深,要刻几方典雅方正的图章,是游刃有余的。而且他在这方寸之地,布局构图,别具匠心,刀法的遒劲,更是难得。
在篆刻中正如他的诗、画和文章一样,章法谨严而又恣肆汪洋,在小小的方寸上也可见他那热情洋溢却并不失于放荡的性格。作为艺术,这可算是上乘了。但是闻一多先生并无意从事这种艺术创造,而是靠这个卖钱,以补经济上的困难,叫妻子的病能够得到治疗,孩子们能够吃饱肚皮,使一家免除冻馁之虞而已。
他的时间本来可以多用来研究中国文化,他有许多成竹在胸的著述需要动笔,然而不能。为了活命,不得不从事这样的“小手工业”,真叫斯文扫地。这可算是当时国统区知识分子的悲剧了。
闻一多
闻一多先生刻图章本是雅事,但来求刻的大多是俗人。那个年代,一般有知识修养的人,一天凄凄惶惶不可终日,哪有余钱玩弄风雅,托闻一多先生刻几方图章呢?来求刻图章的大半是那些腰缠万贯,而又慕闻大师之名,想用大师精巧的图章,提高自己的身价。这却苦了闻一多先生。不刻吧,没有这额外收入,而且你挂着牌子,人家按“润例”付钱,真是“规规矩矩和你做生意”,你能拒绝吗?闻一多先生明知这些脑满肠肥的人哪里懂得什么艺术,但是他却从来不苟且,每一方都精雕细刻。他的苦衷是,不向达官贵人乞讨了,却不得不乞灵于那些钱袋,他仍然感觉这是精神上的屈辱。
吴宓教授怒击潇湘馆
吴宓对于中国文学也是很有研究的,他特别看重《红楼梦》,看重《红楼梦》里的众多人物,特别看重林妹妹林黛玉。不仅看重到爱林妹妹,对于林黛玉的一切行径都认为不可更改、不可猜忌到一种神圣的地步,甚至连林黛玉的居室、用具以及侍婢都是必须尊重、不得侮慢的,于是就发生一件趣事。
吴宓
那一天我和几个同学正在潇湘馆“坐茶馆”,还准备吃湘菜,忽然看到吴宓教授提着手棍,气冲冲走过来。他到了门口,大声叫嚷:“你们敢用潇湘馆这个名字开饭馆,这是对林黛玉的侮辱,岂有此理!”于是他不由分说用手棍乒乒乓乓地把玻璃门窗打得稀烂。这馆子的姓江的老板听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出去一看,是吴宓教授,他正在那里为林黛玉而战斗呢。
他质问江某:“你为什么敢用‘潇湘馆’这个名字?”江某答:“我们是湖南人,潇湘人也,所以用潇湘馆这个名字。”吴教授还在生气:“你知道潇湘馆是谁的地方?你们怎用这个来开馆子,侮辱了林黛玉!你们必须改,马上改!”一堂的同学都啼笑皆非,谁敢去和这位著名教授讲理呢?江某也知道这是没有办法讲理的事,只好恭敬地说:“好,我们改,马上改。”吴教授这才消了气,提起手棍走了,还说:“这太不像话,侮辱……”
大家都劝江某:“你就改了吧,潇湘馆可是林妹妹的神圣之地哟。”
一代女才人、散文家杨绛
杨绛是我国有名的女作家,风光美妙的江南的女才子。出身高门,自幼聪慧,毕业于清华大学,中英文精通。很早就创作新剧,蜚声上海剧坛。她当时与也是著名的学者的丈夫钱锺书在上海齐名。但是她比丈夫钱锺书的名气还大一些,所以人们不称“钱锺书的杨绛”,却称“杨绛的钱锺书”。后来是钱锺书成为大学者,出版了学术名著《谈艺录》和文学名著《围城》,蜚声全国,大家才正名称“钱锺书的杨绛”,到底丈夫比妻子更有名了。这曾经是一段文坛佳话,却是逐渐湮灭了。
钱锺书和杨绛解放后都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是研究外国文学的两根台柱子。钱锺书在中西文学的研究上硕果累累,在学术界盛名日升,如日中天,以至形成众望所归的“钱学”专门学派了。此时的杨绛,虽然也从事重要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如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同时也有别具风格的颇为出色的散文作品。至于她也擅长的长篇,除了《洗澡》等三本作品,再未见长篇。很明显,她是为了突显钱钟书而有意“藏拙”的,从这一点更看出她的高风亮节。一代女才人、散文家杨绛,是我久所仰慕的,却无缘一睹风采。
八次全国作代会我去参加了,我以为能看到这位年逾百岁的长者。她却称病未能出席。不久,九次作代会将开。我的身体如好,我会去参加,也许还有机会一亲风采。然而从报上得知,她于2016年5月25日去世了,享年105岁。如此高寿离去,不必惋惜。我忽然心血来潮,作了一首随口溜,以为博笑。
百岁作家有两个,杨绛走了我还在。
若非阎王打梦脚,就是小鬼扯了拐。
途中醉酒打迷糊,报到通知忘了带。
活该老汉偷倒乐,读书码字且开怀。
本文选自《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较原文有删节修改,部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丨马识途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张进
导语校对丨赵琳
福建省柘荣一中赴新西兰开展教育与文化交流
东南网新西兰6月24日讯(特约记者 陈镁燕)6月19至23日,福建省柘荣一中访学团前往新西兰罗托鲁阿男子高中进行教育与文化交流。
期间,访学团通过参加学校晨会、观摩教学、深入课堂、举行座谈等形式,进一步加强两校交流。新西兰富有毛利族民族特色、开放包容、善于启发的教学风格带给中国同行不一样的体验。
观摩孔子学堂陈雯文老师教学活动
观摩美术、音乐课堂教学
双方回顾了两校十年合作办学的历程。领队福建省学科带头人黄济富老师代表中方学校向罗托鲁阿男子高中赠送来自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的“柘荣剪纸”和“柘荣高山白茶”,介绍中国剪纸艺术与茶文化,并盛情邀请罗托鲁阿男子高中师生选择合适机会到中国交流学习。
向罗托鲁阿男子高中赠送柘荣剪纸作品、柘荣高山白茶
双方还就助力学生发展、学生心理辅导、学校合作方向三个层面展开交流。罗托鲁阿男子高中国际部主任Thuy女士对国际学生生活服务保障、快速考取NCEA考试学分、入学奥克兰大学等8所国立大学的学术服务体系作详细说明,校长A.C.Grinter先生介绍办学特色后,对柘荣县第一中学访学团的到访表示欢迎,认为通过合作有助于拓展双方师生的视野,期待进一步的合作,并回赠了礼品。
深入交流
访学团还拜访了新西兰福建同乡会,听取会长苏启族先生讲述乡贤在新创业历史,并就企业文化、教育等问题与同乡会主要领导进行深入探讨。访学团还参观了乡贤、新西兰宁德商会会长黄永富的企业金石集团。黄会长介绍了企业的发展、壮大的过程及远期愿景。
金石集团董事长黄永富先生接受东南网新西兰站采访
金石铝合金门窗厂于2016年成立,坐落于新西兰奥克兰,自成立以来一直加盟于新西兰本地最大的铝型材供应商Altus旗下的Nulook品牌,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飞速增长,在新西兰65家Nulook加盟商中脱颖而出,如今已成为新西兰铝合金界龙头企业。
参观金石集团下属企业
前排从左到右:柘荣县第一中学对外合作处副主任郑慧、办公室主任陈丰、福建省学科带头人黄济富、金石集团董事长黄永富、新西兰宁德同乡会会长王旭、东南网新西兰站站长陈镁燕、柘荣县第一中学教师代表阮锦芬
黄济富老师在接受东南网新西兰站站长陈镁燕采访时表示,学校将加强校企交流,为学生开展国际研学活动开辟新的途径。
黄济富老师接受采访
柘荣一中中新合作办学项目联络人、新西兰宁德同乡会会长王旭先生全程陪同此次教育访学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