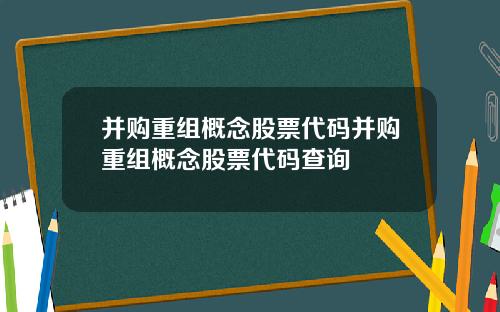我的大学生活 一周4次核酸
作者 | 路迟
开学一个月了,四川的大一学生杨木只上过一周线下课,一共做了7次核酸。“感觉被一种从未有过的莫名力量困住了。”
“没有疫情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这个问题困扰着很多和杨木一样的大学新生。
辛晨是在江苏一高校的准毕业生。她怀念疫情爆发前的大一,那时候,她可以随时奔向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青春才几年,疫情占三年”,一句感慨透着许多应届大学毕业生的无奈。也有同学乐观地把疫情视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催化剂,让我们更早懂得责任和担当。”
一周四次核酸
“一想起大二以来做过的核酸,喉咙里就长满了棉签。”
南京大学文学院的研究生顾阳哭笑不得地形容。自3月14日封校后,一周内她已经在校做过4次核酸了。一个多月过去,学校只解封了不到三天。
他们待在宿舍里,等待着混检和封校的反复到来。
“混检”,就是将学生分成小组一起抽查检测,如果里面出现一个阳性,一整个组就都要被隔离。
大学校园的临时检测点,师生在进行核酸检测(来源:视觉中国)
3月15日凌晨三点,上海的大一学生林浅浅忽然被辅导员的电话叫醒,学校里出现了密接,因此得向每个学生确认行程。次日早上8点开始,全校再次封闭,课堂重新搬回网上,宿舍成了学生们唯一的活动场所。
林浅浅的同校朋友何帆,是在上马原课的时候忽然被通知复检,原来前一天的十人混检里出现了阳性,何帆和同班三个同学检查完后被安置到一间空教室里,晚上他们就在教室里打地铺睡了。
2020年1月初,病毒最先在武汉发作,华中师范大学的李青然正在备考。但当时,李青然对此无感,疫情,还是太陌生了。
直到考完试回家过年,李青然才意识到形势的严峻。
“出现人传人”“无症状感染者”,李青然脑袋大了:我不会携带病毒吧?
那个春节,她不敢出家门半步,天天盯着疫情新闻,“更不敢告诉别人我在武汉读书”。紧接着,武汉返乡群体成为重点关注对象,社区开始频繁打电话、上门量体温。
2020年6月6日,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大门口,毕业年级学生返校通道(来源:视觉中国)
原定返校时间被无限推迟,一停就是一整个学期,连带着一个暑假。直到2020年秋季,学校才通知他们分批返校。
回到阔别大半年的校园,李青然发现周围一切都被拉上了一层保险杠。
进学校不能再仅凭一张学生卡,而是要核酸阴性证明、返校申请证明、排队量体温。宿舍楼里多了每天更换的消杀报告,学院给每个人都发了口罩。
多数大学采取半封闭措施,出校门必须向学校报备和申请,审批通过后才能凭条出入。
辛晨所在的学校对请假条的审批要求严格、进度也慢。一次,辛晨的手机屏幕碎了,出校审批等到两天后才下来。
有段时间,外卖进不来,食堂禁止堂食,但可以点外卖送到学生宿舍,有些饭菜也涨价了,十元一份的炒粉涨到十二元,包装盒还要多加两元。
2020年5月19日,广西桂林,受疫情影响,大学开学后采取了只进不出的政策,不能进校园的外卖小哥只能在大门外“递餐”(来源:视觉中国)
2020年下半年,是李青然所在学校迄今为止校门持续开放最长的时候。那个学期,武汉的疫情平息,出入限制也少了。
“但好像没有几个人愿意出去了。”她说。
网上做实验
辛晨念大一时还没有疫情,每学期每门专业课都会有对应的实验课程,2020年开始,实验课全部变成了“老师在线播放实验视频”。只能看,不能上手做。
好在,辛晨的专业课老师把大家错过的实验都安排到了返校后的下学期,但得用周末时间来补,实验流程也被大大压缩了。
当然,学生要付出的精力和时间也是加倍的,“从早上七八点到晚上八九点一直待在实验室”是辛晨那段时间的常态。
李青然读的是文科专业。疫情之前,学生每年寒暑假都会有机会去香港、台湾交流实践,但疫情爆发后,出境变得不可能、跨省也有很多顾虑,线下实践学习的机会几乎被一砍没,去乡镇、社区调研的机会也少得可怜。
学生写的研究论文也变得“不可信”了,“老师学生都知道这篇报告根本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没有实践调查为支撑。”李青然说。
研究生顾阳的研究方向是古代文学,但疫情爆发后第一个学期待在家中,很多古文献、古籍还没有电子化,没法去学校和图书馆查。
学校举办的很多名人讲座也搬到线上了,比如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历史学者仇鹿鸣、作家勒克莱齐奥……都是那种如果面对面会很让顾阳激动的前辈大咖。
大学老师通过网络向学生授课(来源:视觉中国)
被疫情隔离的还有校园恋情。23岁的余蕾在长沙读完本科后,2021年考上了广东一所高校的研究生。本科期间认识的同校男友原本说好今年五一节来找她,但看样子悬了。
陕西的大二学生方源与女友在同城相距6公里的大学就读,两个学校都封闭后,原本10分钟车程就可以到达对方身边的距离,变成了无限期的电话、视频和文字聊天。
成长的催化剂
悠悠参加了2020年的高考,最后半年里,她这样总结:“二月的疫情、三四月的网课、五六月的冲刺。”
九月去大学报到时,校门口的志愿者问她:“吃饭了吗?进校之后就不能出来了哦。”悠悠的父母也被堵在校门外。
三年前,悠悠的姐姐上大学时,全家人送姐姐到宿舍楼下,再帮她把行李一件件搬上去,一起参观学校。轮到自己时,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和记忆。
2020年10月13日,郑州某大学新生报到期间,出于防疫需要,新生的家人不允许进入校园,学生进入校园后,家长隔关大门或目送孩子进入校园(来源:视觉中国)
直到大二结束,学校依然持续处于“封校-短暂放松-封校”的不定期循环状态,出校门都必须要假条。
两年过去,悠悠对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一无所知,没去过任何景点,不了解地铁线路和公交站,不知道学校周边有哪家超市、哪些餐馆,“甚至连去校本部的导航都能走错。”
一晃就大三,悠悠毫不夸张地觉得,“仿佛昨天才刚刚入学报到”。她不知道,“从未拥有”和“得而复失”,哪一种更幸运。
体会过“正常的”“自由的”大学生活,那种失落感会更强烈。
18年入学的辛晨,在大一一年就游遍了长三角各省市;大二申请到了美国的“带薪”交流项目,被加州的阳光晒得黢黑;那年国庆,她和朋友到上海去疯玩,为了等薛之谦的演唱会吹了一夜寒风。
2020年开始,辛晨每年都会参加的羽毛球比赛、歌唱比赛和各种交换项目也都砍掉了,目前大四的她,也不再能按照原计划申请出国留学。
但校园生活还在继续,也有人创造着另类的记忆。
2021年12月18日,高校学生遵守防疫规定戴口罩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来源:视觉中国)
3月底的一天,梁钰帮同学过生日,出不了学校、校园食堂不允许堂食,为了能尽可能给朋友营造一个生日氛围,梁钰在学生部门仓库里搭起帐篷,再在校外定制了一个生日蛋糕,在帐篷里点起了蜡烛,开Party。
“在餐厅过生日的大学生有很多吧,但在仓库里过生日的,我们大概是第一个。”梁钰颇为自豪地笑道。
梁钰想到了自己的爷爷奶奶,他们的青春留在了戈壁滩上的生产队。“爸爸妈妈也有着他们青春时期的特殊设定,只是恰好,我的设定停在了‘疫情’上。”
梁钰乐观地把疫情视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催化剂,让我们更早懂得责任和担当。”
她想着,以后可以对自己的妹妹讲,“你不知道吧,姐姐的大学有一整个学年都是在家上课的哦,姐姐甚至一边炒菜一边上课哦!”“我们那个时候啊,还可以去社区、学校做志愿者,来保障大家的健康,是不是超酷的!”
学会平静
3月14日早晨,上海交通大学大三学生谭星从宿舍床上醒来后,忽然发现自己所在的宿舍楼被封了。
从这天开始,她看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另一个交大。
辅导员、教职工轮番给学生送物资和食物,教授们开着私家车给学生送餐,午晚餐的配餐标准是10-12元,但每一餐都包含三荤两素,五块钱的早餐里包含了定价六块五的牛奶。
“以前去星级酒店奶茶店网红店都不拍照的,现在每天都在记录今天又吃到了什么爱心盒饭。”因为快递进不来,谭星最大的乐趣变成了拆每天配餐的“盲盒”。
校友也捐来各类物资,包括卫生巾和泡腾片……她能理解一些学生对封校的不满,但谭星更愿意在特殊时期调整心态,“感谢母校,把我们保护得都很好。”
大学后勤人员和学生志愿者正在搬运物资(来源:视觉中国)
疫情阻断忙碌的校园生活,也让人思考“大学的意义”。有人抱怨网课让大学质量大打折扣,但“就算天天到教室去上课,哪个学校没有混日子的人?大学终归是给自己读的。”梁钰坚信。
在疫情中完成大学学业,开始被这一些学生理解为自己的独特遭遇。就像甘雨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的:“疫情对我们来说是一场苦难,但我不得不承认,经历过它,我才真正学会了怎样才是平静、怎样才能平静。”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均为化名)